她,1933年出生于北平,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
她,先后在检察院、法院、律师协会工作。
她,成为“文化大革命”后北京的第一名律师。
她,推动并引领了北京律师改制工作。
她,被称为“北京第一律”。
她,就是北京“终身荣誉律师”、原北京市司法局副局长周纳新。
指天慨叹:律师梦难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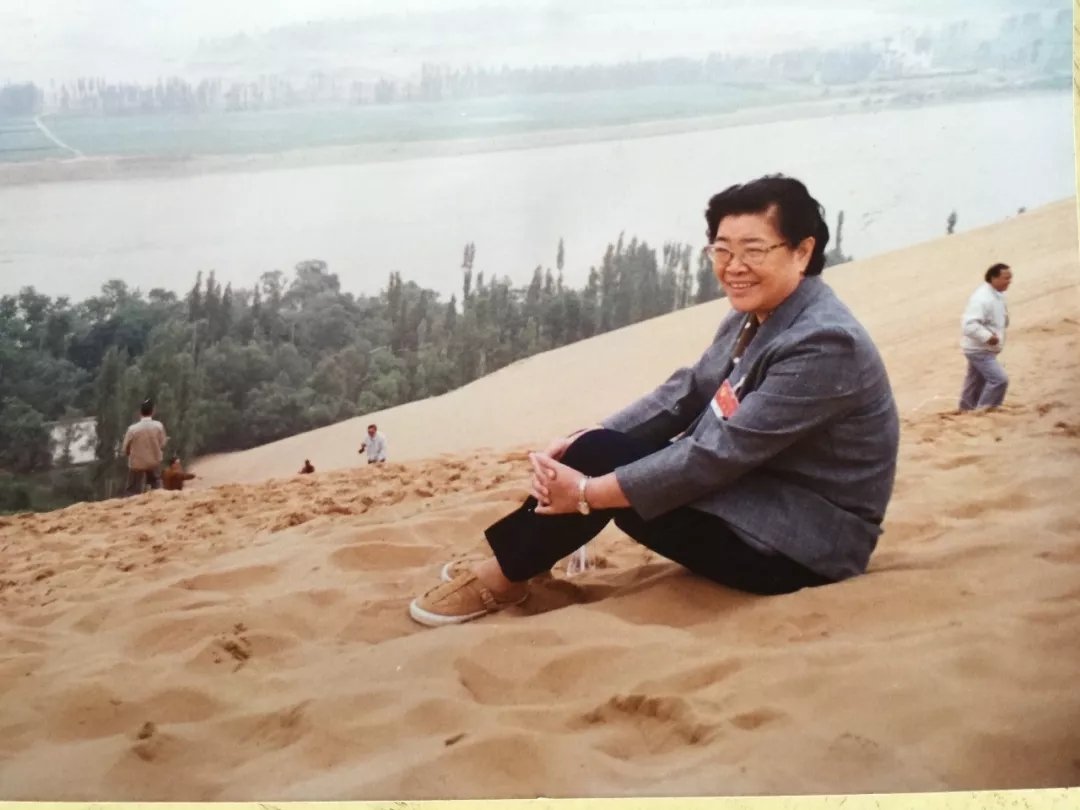
1948年,15岁的周纳新在北京慕贞女中读高中。读书时,她喜欢看一些侦探小说或者律师辩护的故事。尤其是一个重大案件的成功辩护,影响了周纳新一生。当事人家属为慎重起见,聘请了上海、苏州两地21名律师组成了庞大且豪华的律师团。他们的名字如雷贯耳,个个都是法界名流。经过辩护,最终使当事人无罪开释。
这个案件让周纳新觉得律师正义、仗义、公正,胆子大,敢说敢干。她因此下了当律师的决心,坚决要考法律系。
1951年,周纳新高中毕业,考上北京大学法律系。1952年,北大、清华等几所院校的政治法律系合并成北京政法学院,就是现在的中国政法大学。1954年,周纳新从北京政法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河北省人民检察院工作。
虽然服从组织分配进了检察院,但是周纳新还是想做律师。她不断地向组织要求,一年多之后,她被调回北京市律师协会研究室工作。
当时,北京有100多位律师,但专职的只有40多位,其余的都是高校老师兼职。
好景不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周纳新在北京市崇文区人民法院做审判员。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些年,周纳新带领知青去插队,到延安待了三年。平日里,她带着一帮小孩子上山砍柴、下河挑水,修梯田、烧石灰,拉着石头到县城去卖,尽力帮助农民改善生产、生活。
晨光初曦:北京律师有家了
1970年,周纳新回到北京,去了崇文区劳动局,在那里专门负责安排回城知青的工作。
1978年年底,北京市召开司法工作会议,决定先恢复律师制度,开展律师业务。这项工作由北京高院司法行政处负责管理,恢复律师制度需要律师,北京高院一位副院长找到了周纳新。她回到了北京高院,成为“文化大革命”后北京的第一名律师。
周纳新回去后,让组织将在北京高院工作的一位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生江浩调过来做律师。这样,北京市就有了第二名律师。在司法行政处办公室的一个角落,有两张小桌子,周纳新和江浩一人一张桌子。北京律师,就从这两张桌子开始重新出发了。
1978年12月12日,周纳新代理了中国律师制度恢复之后的第一起刑事案件——丁某盗窃案,这也是全国范围内第一次有律师出庭为被告人做辩护的案件。全北京市公检法的几百名干部、《人民日报》等许多媒体记者旁听了庭审,《人民日报》头版对庭审情况做了全方位报道。
1979年,七部意义不凡的法律破茧而出,中国法治之旅开始破冰,北京律师业也快速发展。
1980年8月26日,关于律师制度的第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以下简称《律师暂行条例》)获得通过。1980年11月,司法部发出《关于下达审批律师资格试行办法的通知》。
1981年5月7日,北京市司法局根据《律师暂行条例》的规定,结合1979年律师制度恢复时期的状况,正式批准授予周玉玺、傅志人、周纳新等41人律师资格。这是北京市首批授予律师资格的人员。
北京市律师协会筹建三年后,于1982年4月12日召开了北京市律师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召开,是北京市律师制度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它庄严宣告:北京市律师协会正式成立。
从这一天开始,北京的律师们终于有家了。
涛头独立:改革大潮不可阻挡
北京市律师协会成立和《律师暂行条例》的颁布,推动了北京律师乃至全国律师的恢复步伐,律师队伍迅速壮大,律师事务所数量得到很大发展。
1986年,周纳新出任北京市司法局副局长,分管全市律师与公证工作,不再做专职律师。从此,周纳新与全国律师一起站在律师体制改革大潮的潮头,为中国律师从国办所到合作所,从合作制到今天的合伙制,闯出了一条发展道路。
1986年后的中国进入改革发展快车道。与此同时,社会对律师的需求增大,而律师却非常少,供求严重不平衡。北京市司法局想了不少办法,律师们加班加点,但这个问题仍然得不到缓解,该问题也引起司法部的重视。1987年,司法部把一份关于律师体制改革的报告上报国务院。不久,国务院批复: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做改革试点。
司法部的改革方案力度相当大:新体制下的律师事务所,不占国家编制、不要国家经费,实行“四自”——自收自支、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
这样的变化,堪称历史之变。作为那段历史的先行者,周纳新称自己心中曾有忐忑:“北京市司法局经过研究,决定在全国带头先行做律师体制改革的试点。改革之门被推开的刹那,我心里没有底。按照司法部改革方案的要求,新体制下的律师必须辞去公职,不拿工资,不享受公费医疗和一切福利。”
北京市司法局为此专门召开了一场动员大会。在会上,周纳新做了动员。不久,当时担任北京市第一律师事务所副主任的王以岭律师第一个报名。
1988年7月28日,北京市第一家合作制律师事务所——北京经纬律师事务所成立,这标志着律师的“铁饭碗”就此被打破。
当年年终盘点,合作制律师事务所的业绩出乎意料:与国办律师事务所相比,王以岭等人开办的经纬律师事务所的效益要好得多。北京市第一律师事务所的20多位律师一年赚了30多万元,而王以岭等五个人半年就赚了26万元。于是,在不长时间内,北京把合作制律师事务所的数量扩展到了4家。
就这样,北京的律师工作走在了全国的前列。1992年,北京市司法局新批了26家合作制律师事务所。这样,7家国资律师事务所和合作制律师事务所在北京并存。
1993年,北京市司法局开始合伙制试点。这意味着,我国的律师体制真正与国际接轨。个人合伙的性质,产权归合伙人所有。
1995年,全面的律师体制改革在全国范围内推开。无论是国办所还是合作制所,全部改为合伙制律师事务所。
对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周纳新给予了高度评价:“合伙制非常好。这些律师事务所有后劲,想办法开拓业务。比如说,现在大家最关心的买方贷款买房,就是经纬所开发出来的业务。”
1996年5月15日,《律师法》获得通过。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律师业开始走上大发展、大繁荣的道路。
桑榆未晚:法律援助实现全覆盖
1998年,65岁的周纳新从北京市司法局副局长任上退休。
2009年,在纪念律师制度恢复重建三十周年纪念会上,周纳新和另外15位律师被北京市司法局授予“终身荣誉律师”称号。
周纳新在退休后花更多时间专注于法律援助公益事业,并挑起了北京市法律援助基金会理事长的担子。她看到,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的法律基础比较薄弱。一些人由于缺乏法律意识,不知道寻求法律帮助,因而导致不少悲剧的发生。
周纳新说:“我退下来以后,开始做法律援助工作。我调查的非常仔细,一直到了最深的基层,到经济比较落后、最基层的地方调查。为什么我这么大年龄还下这么大决心去做这项工作?到这些地方调研以后,我才发现北京市到那时为止,还有很多法律服务的空白点。我在基金会干了四年,把钱给了最穷的地方。我用四年时间,抓了五个落后区县。这五个落后区县,每个村、每个乡镇都成立了这样的法律援助基金会咨询站。”
在周纳新的推动下,法律援助拓宽了服务面。北京市大力推进法律服务进社区工作,法律援助的项目包括为农民工、残疾人服务。
现在,北京的法律援助工作得到了各方的支持和认可,覆盖面更广了。全国各个省市区都和北京一样,将法律援助扩展到很多方面,每年都有很多人受益。谈到这一点,周纳新深感欣慰。